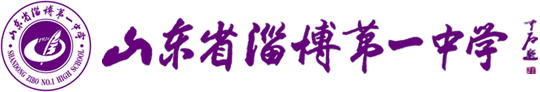洗凡中学校长徐佛千
王 济 世
1948年下半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博山私立洗凡中学的负责人徐佛千、赵蔚芝带领部分教职员工和全部校产并入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淄博中学,即今日的名校——淄博一中,从而在人民教育事业中获得新生。时任洗凡中学校长的徐佛千先生,是博山知名教育家,在学校面临重大抉择的生死关头,发挥了自己的重要作用。
徐重印(1904-1962),字佛千,出生于博山西冶街著名书香门第,其祖父徐丰元、叔祖徐旋元在清末光绪年间先后中举,其父辈徐宝田、徐宝三、徐宝恩等亦都是清末民初博山知名人士。他的父亲徐瑞桢,是徐丰元长子,终生为人做账房先生。由于家庭熏陶和父辈影响,徐佛千幼读私塾,后外出求学,于1921年毕业于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早年曾任博山职业补习学校、怡园小学校长。“七•七”事变前,曾任日照县政府第四科科长。抗战期间,积极参与国民党敌后政权的抗日工作,任山东赈济会干事,参加过县长培训班学习。其间,在返济探亲时,曾遭日伪逮捕入狱,被在济南经商的二兄徐重兴保释出狱。由于奔波于抗日工作,家里老婆孩子无法顾及。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山东省民政厅视察兼洗凡中学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淄博一中任职员,长期从事发通知、刻钢板、写会标、干点零碎事务工作,守职尽责,默默无闻,十年如一日。晚年患鼻咽癌,于1959年退职,1962年病逝。
洗凡中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4年的燕山中学。抗战期间停办。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在济南恢复,直到济南解放。徐佛千是临危受命,担任洗凡中学校长的。1947年暑假,洗凡中学第二任校长贾聿策(字慕夷,又慕谊,博城大核桃园人,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是博山教育先驱、燕山中学倡办人之一,时任山东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是在野派参议员首领),因痛恨反动当局诡诈欺骗,气恼郁结,突患脑溢血去世。洗凡中学的政治靠山和经济募捐者倒了,许多麻烦事却接踵而来,校长位子空了三个月,由教导主任赵蔚芝代理,总非长久之计。于是,由蒋洗凡的弟弟蒋敦鲁(谱名衍临,早年在济求学,1926年加入中共,曾任博山支部第一任书记,后脱党)出面保荐佛千为校长,得到校董会的同意,于是徐以省民政厅视察身份兼任了洗凡中学第三任校长。这时洗凡中学已非昔日,危机重重。首当其冲是校舍纠纷。当时洗凡中学在济借用校舍,包括冀辽同乡会和北宁小学两部分。当初借用,同乡会就不同意,碍于贾慕夷面子,勉为其难,贾死后,他们百般刁难,告到法院,收回了两口教室,迫使洗凡中学腾出女生宿舍,将三间满地是水的破屋铺上木板当教室;再是经费无着。开始复校时,学生不收学费,后来每人每学期学费收一袋面粉。贾去世后,改收1.5袋面粉,经费入不敷出。徐便同大家商议过紧日子,教职员工待遇先照顾兼课的,再照顾专职的,先照顾外籍教员,再照顾博山籍教员。到了最后,几个博山籍教职员工仅能吃上饭;另外,学生大量减员。洗凡中学设在济南,但生源来自博山。学生人数由开始的230余人,减到160余人。新招的初中班,济南当地学生多,博山籍的少。原因有三:嫌离家远,学费增多,国民党军队诱骗入伍。面对上述状况,洗凡中学很难在济继续办下去。这时,政治靠山贾慕谊去世,梁绪恩虽在济南,但无法解困经济,唯一出路,是把洗凡中学迁回博山。但由于当时许多人脑子里“正统”观念严重,对解放战争局势等待观望“局面安定”,因而何去何从,摇摆不定,徘徊不前。但1948年九月,我华东野战军一举解放省会济南,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强大威力,鼓舞了山东广大军民。同时,解放军的炮火也震醒了洗凡中学的有识之士。校董会和校负责人决定,由徐佛千和早年就与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有过来往的博山籍教师王克常负责回博山找人民政府教育部门联系。当时博山已经解放,看到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百废俱兴,人民政府深得人心,徐、王深受教育。党领导的淄博中学派张凌云同志与徐佛千一块返回洗凡中学,为教职工支付了三个月欠薪。于是,洗凡中学负责人自愿请求并入淄博中学。于1948年底把全部校产运回博山,交给淄博中学使用。原洗凡中学徐佛千、赵蔚芝、李新寰、王克常、赵学周等8名教职员工,先后进入了淄博中学工作,成为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教师队伍一员。博山私立洗凡中学,也圆满地完成了她的光荣历史使命。
徐先生等人进入淄博中学后,按各人业务专长安排了工作。徐佛千被安排在教导处做一般教务工作。赵蔚芝、王克常等人又回到了教学岗位。赵后来从淄博一中调淄博师专,成为教授、我市研究赵执信、蒲松龄的知名大学问家,曾任淄博市政协5——6届副主席;王克常先后在淄博一中、淄博十三中、淄博三中任教,为博山区政协1——6届委员,淄博市政协三届委员。当年洗凡中学带过来的那辆胶轮马车,一直在为学生食堂买菜运粮,直到1959年大炼钢铁时还去八陡等地运焦炭、矿石,至今为众多老校友所记得。
徐佛千为人宽厚,在从教生涯中,经常帮助接济家境困难学生,当有的青年学生由于追求进步活动遭到反动当局拘捕后,他千方百计联络社会名流士绅保释他们。在他晚年,同淄博一中艺体美术教师、山东省首届文代会代表林笃泉先生,工作之余,在柳杭村水河方家园饲养了几箱蜜蜂,潜心研究摸索养护技术,观察这些小生灵的生活习性,并同在此种菜的王育臣先生切磋饲养奶羊和种植引进无花果、菊花、番茄等花卉蔬菜新品种技术等。先生学识广博,书法也颇有功力,尤其小楷,端庄清秀,苍劲饱满,可惜作品存世不多。由于当时环境及他本人一生严谨,著述甚少。值得欣慰的是,近日淄博一中在筹备85周年庆典过程中,于市档案馆查阅到一份60年前《洗凡中学十八级同学录》,弥足珍贵。内有徐先生撰写的序文,文章虽短,但思想深邃,语言精辟,可谓社会改革浪潮中毕业学子的感悟箴言,同时也可从中一窥先生的理念信仰与文笔风采。
《洗凡中学十八级同学录》序:
前校长贾公去世后之三月,余以诸学董不释之故,获长斯校。视事凡八月,而逢十八级同学毕业之典。时逝如川,昼夜兼程;诸同学从我既暂,再晤且难,分手之际,可无一言?今既以齿录之序属余,爰将所欲言者书以为序。临别之赠,愿各勉焉。
书云:满招损,谦受益。满者,自限之谓也。吾同学毕业之后,或升学,或就业,当思学无止境,德无止境。尤勿画地自限,故步自封。旷观今日之学术,浩如渊海;反视古人之修德,日新又新。圣如孔仲尼者,且思五十学易,庶可免过;贤如蘧伯玉者,尚当半百之年,而省四十九年之非。圣贤以天纵之资,犹且好学如此,敦品如此;矧平庸如吾侪者哉?此吾所以持戒自满为诸同学告者一也。
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馁者,自怯之谓也。吾同学毕业于家乡变革之际,战云紧张之时,以言上进,则极目荆棘;以言服务,则头神无门。升学转为辍学,毕业顿成失业。然人生处世,意志决定一切,精神振奋,竭力以赴,则前途荆棘,正赖吾等斩除;谋生之门,正赖吾等开辟。又何忧上进无路,服务无由也哉?此吾所以持戒自馁为诸同学告者二也。
古人有献芹献曝之说,事虽可笑,意出于诚。诸同学其以斯言为芹,而一尝其味;其以斯言为日,而一受其曝。可乎?
(根据先生后人口述及有关史料整理)
王济世,中共党员,1963年毕业于我校初17级。曾任博山区委党史委主任、博山区档案局局长。参与主编了《中共博山党史大事记》等史书。发表文学作品数十篇。荣获淄博市党史、档案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被省人事厅、省志编委荣记三等功。